“周扒皮”和“半夜雞叫”,都係根據需要製造出來的。具體過程,簡單地講,“周扒皮”的製造經過係這樣的:1950年代初期全軍全國範圍大掃盲。文盲戰士高玉寶表現積極,用畫字的方式寫自傳。被部隊推為典型上報。窮苦出身的戰士不僅學文化還能寫書,批判舊世界歌頌新世界。為了把這個典型放大,部隊派專業人士幫助高玉寶。要體現舊世界之黑暗,地主階級之罪惡,為了使書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頭換面進行深加工。為了表現真實,書中一切都採用真名真姓真地點,自然發生的“故事”就係真實的。至於壞地主半夜學雞叫,純屬靈感來襲。郭永江其子女介紹,其父荒草晚年講過,“半夜雞叫”係根據民間傳講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半夜雞叫》英文版封面
眾所周知,在過去的60多年中,影視、文學作品與似史非史的各種敘述,將“周扒皮”與“南霸天”、“黃世仁”、“劉文彩”並列為“四大惡霸地主”,係舊社會剝削階級的典型代表,在樹立“新舊社會”好惡觀念中,可謂標誌性符號。
“周扒皮”這一人物,最初來自自傳體小講《高玉寶》。《高玉寶》係一部獨特的作品,書名即主人公之名,也係該書作者的名字。此書人物均用現實中的真名真姓。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也被真名實姓寫進書中,被賜綽號“周扒皮”。出於時代政治需要,該書被推向全國,編入教科書,產生了巨大影響。
與其他文藝作品不同,至今仍健在的《高玉寶》作者高玉寶堅稱書中所寫為真實事件;而且多年來在大陸各種新舊社會對比性質的敘述、教育、展覽中,《高玉寶》一書中的許多內容又常被作為真實的歷史來看待。尤其係“周扒皮”半夜學雞叫逼長工下地幹活的故事,一直令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
因《高玉寶》一書,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後人大受牽連。改革開放之前,與“四類分子”(地富反壞)的後人一樣,歷次政治運動中,均成為被運動對象,備受歧視和冷遇。
“半夜雞到底叫沒叫?”“周扒皮何許人也?”“《高玉寶》一書如何成書?”連續有五年時間,我為此到處奔波,收集資料,逐一進行了考證。
我在自己所寫《半夜雞不叫》一書中最終向世人還原事實真相:周春富,遼南農村的這個勤儉吝嗇到極致的小富戶,既唔係為富不仁作惡多端的惡霸地主,也唔係在傳統農村佔有積極影響的鄉紳,他只係在新舊政權交替的土地革命運動中不幸死於激進的批鬥之中的小人物,後來因為一部自傳體小講《高玉寶》而為人所知,成為家喻戶曉的“地主”代表。這個在意識形態的層層油彩中成為特殊年代階級教育的反面典型,係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各種因素、要件集納在一起“加工定製”而成的產品。所謂“半夜雞叫”,純屬虛構。
起意追尋真相
我的家鄉在遼寧復縣(現大連瓦房店),嗰度就係“半夜雞叫”故事的原產地。
“周扒皮”和“半夜雞叫”的故事曾陪伴我度過屈辱、自卑的童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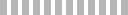
因得到早教,我七八歲就認識很多字。我到鄰居家玩,鄰家的大孩子經常特意給我看課本中的《半夜雞叫》,我當時覺得這個故事特有意思,唔識的字還向對方請教,在讀到小玉寶用計痛打“周扒皮”時,我會與其他孩子一樣哈哈大笑起來,儘管我當時不太明白,為何一向吝嗇的鄰家孩子,每次都會慷慨地借給我課本讀這篇課文。
一次,在跟村裡孩子吵架時,嗰啲孩子突然指着我喊“周扒皮,周扒皮”,我突然意識到,自己母親姓周,進而鄰家孩子以往古怪的笑容也浮現在我眼前。我倉皇逃回家,問母親“咱家係咪‘周扒皮’?”,母親先係一怔,然後重重地給了我一耳光。我哭得很傷心,母親摟住我,跟我一起哭了起來。
此後,我變得敏感、自卑甚至低人一等。上小學四年級時,打開新發的語文課本,我發現自己最不願見的那篇文章《半夜雞叫》赫然出現在課本中。
上這一課前,我有一種大限將至的感覺,希望自己病倒,希望老師有事。沒想到,上這一課的那一天,老師第一個便點了我的名字,讓我朗讀課文。我搖搖晃晃站了起來,含着淚水讀完課文,兩腮發燙。那一節課老師在講咩,我已無心留意,但同學們的竊竊私語我卻聽得很清楚,同學們都顯得興奮,因為他們親眼目睹和證實了一個傳聞。
時光一轉眼到了2003年初,互聯網早已興起並普及,我在大連地方的門戶網站“天健網”發了一篇5,000餘字的帖子,名為《故事和“半夜雞叫”有關》,講述自己母親家族的啲見聞。論壇一下喧囂起來,參與討論者甚眾,形形色色的觀點和傳聞紛紛登場。但當時國內將要召開一系列重大政治會議,各級宣傳部門嚴把輿論關,這個帖子最終因為涉及敏感歷史問題而被刪除。
這件事給我震動很大。老實講,自己家的事知道啲,不過要讓我把“半夜雞叫”有關的整個大背景的來龍去脈講個清楚,道個明白,那時的我卻沒有這個能力。高玉寶怎麼從家鄉走出去的?曾外祖父的命運與時代有何關係?《半夜雞叫》的故事如何走向全國?那時我對這些事也只有啲模糊的印象和似係而非的概念。此事讓我決定冷靜下來,去思考啲問題,追尋逝去的歲月,考證細節的真偽。
我因此展開了一項行動,追溯並考證家族的歷史。自打那時起,我幾乎所有的雙休日和節假日都用於出入於各大圖書館、檔案館、舊書市場,採訪親屬、朋友和當事人,請教史志專家,刻苦閱讀歷史、政治、軍事著作,甚至還學習與“雞叫”有關的動物學、氣象學以及農學知識。
這種考證對我而言係異常吃力的。首先要了解時代大環境大背景,然後係具體事件和具體人物。家鄉歷史涉及民國、偽滿、內戰、土改、社會主義改造、人民公社、改革開放新時期等階段,需要在此背景依託上,細看遼南鄉村的種種生活細節,土改前後的變故、掃盲運動中典型的誕生以及工農兵的時代印記等等。
所幸,漸漸從雜亂到理性,從混沌到清晰。
“周扒皮”其人
我對曾外祖父周春富的所有認知,均來自周家後人、舊鄰的回憶和幾位在世長工和短工的描述。
家裡已經搵唔到一張他的照片。在1947年的土改運動中,他在1911年建的幾間石頭房和所有東西被分光,房子分給一戶貧農居住,至今保留在瓦房店閻店鄉,成為嗰個村子最老的房子。呢度現住戶叫高殿榮,我2006年第一次見到她時92歲。她回憶,當年呢度原先分給一戶貧農住,人家嫌房子不好,佔了她家的房子,把她攆過來住。她家當年成分也不好。她回憶周春富:人不惡,係好人。
曾外祖父周春富原來也係闖關東落戶遼南。通過勤儉持家,不斷攢錢買地,開了幾個小作坊,成為殷實之戶。至上世紀40年代末期,家裡已有近200畝地。家裡有五男三女,有大有小,地里和作坊忙不過來,就陸續雇起長工和短工。老頭僱人的一個條件就係要求莊稼活好。
曾外祖父人勤儉仔細係有名的。兒女們有這樣的印象,係因為老頭不僅對自己特別摳門兒,對家人更係如此。碗中剩下的粉條,得撈出來晒乾,留着下一頓吃。老頭向兒女們提倡:飯要吃八分飽,吃多了,剩下的都成臭屎。出嫁的女兒回娘家不能過夜,因為這樣會多吃一頓飯。相反對長工一直很客氣。
王義楨1942年開始,給周春富做過近兩年長工。我先後三次見過他,他能對我很清晰地回憶老東家:
我去那年,(周春富)老頭60歲。不閑着,鍘草他幫着續草,他續草鍘出的苞米秸長短勻齊,牲口愛吃。夏天上身不穿衣服,後背曬得黑紫黑紫的。人會打算,仔細。老頭有個特殊要求,夥計也好,兒女媳婦也好,不準穿紅掛綠,幹活怕沾灰就不能撒手干。我20出頭,老媽給做件小白褂。老頭講,王夥計給你染染吧,唔好你錢。都講老頭狠,那係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沒講過我咩,我單薄,但會幹。老頭講,會使鋤、能扛糧就行。老頭對兒女嚴,人家院子里係不能有雞屎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鏟子往院坑裡拾掇。家裡不養牛養騾馬,腳力快也乾淨。我在他家早起係不假。人家養成了習慣,冬天天沒亮點了火油燈,家裡人做飯的做飯,喂牲口的喂牲口。人家都起來了,你夥計還能賴在被窩裡嗎?起來沒有事挎着筐揀狗糞。
曾外祖父家鄉復縣閻店鄉和平村黃店屯,在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境內。東北光復後,國共兩黨在復縣城鄉,展開血腥殘酷的拉鋸戰。
我後來在瓦房店縣誌中看到,當年復縣有耕地200萬畝。全縣9萬戶,地主佔2,000戶,富農7,000戶。頭三號地主都有幾千畝以上土地和其他財產。周春富還屬於富農行列,但擁有土地不到200畝。因此可以算出他在復縣財富榜上的位置,應該排在2,000名之外。
後來土改糾偏,曾外祖父再次被劃為富農。瓦房店檔案館現存原復縣閻店鄉的1960年的“落改”材料證實周家的富農身份,這也係我在搜索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資料時唯一見到的“文獻”。
在這份紙張發黃的手寫落改報告中,列舉了有220戶的和平大隊的七戶地富反壞分子和新畦三名地富反壞分子作為“敵人”的活動情況。曾外祖父三子、本人外祖父周長義的名字赫然列入其中。開篇的背景文字直接提到,和平大隊解放前深受日寇和國民黨殘酷統治,廣大勞動人民在臭名遠揚的“周扒皮”等封建惡勢力的壓榨下,民不聊生、不得溫飽、逃荒甚多……
當年土改時,從方法到概念,均效法蘇聯,把相關的意識、話語植入農村;中國農村原來以宗族、學識、財產、聲望為根基的鄉村秩序,均被階級意識和話語所顛覆。曾外祖父周春富只係在這場暴風驟雨運動中的一個不幸的小人物,不過老頭自己卻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死後卻成為“惡霸地主”的典型之一,聞名全國數十年。
半夜,那雞到底叫沒叫?
《半夜雞叫》中的地主周春富,係我曾外祖父的真名實姓。在書中,周春富因“殘酷剝削”長工而有“周扒皮”綽號,為催大家早點上工,半夜躲進雞舍學雞叫,引起公雞們打鳴,後遭小玉寶設計痛打,這係其中最生動、最著名的情節。
近年來,有不少作者撰文指出,無論從農學、動物學和當時農村普遍租佃關係的史實來看,這些細節都與事實相悖。大連地區養雞30年的高級畜牧師房司鐸做過研究,他曾給我做過科普,他認為公雞啼鳴有兩個必要條件,一係必須係成年公雞,二係必須自然光感刺激。遼寧南部農村鋤地一般在小滿、芒種至夏至季節進行,日出時間係早上4時28分。黎明出現在日出前一個小時,亦即早上3時30多分鐘,太陽微弱的輻射光即可對雞的視覺發生刺激,產生啼鳴條件反射。但這時的光線很弱,人的視覺還不能對物體的細小特徵進行識別。所以在半夜三更(即午夜12時),在一片漆黑條件下,更不能從事田間操作了。就算係把長工趕到黑燈瞎火的莊稼地里,也只能係要長工換個地方繼續睡覺。
從上世紀40年代初到1947年遼南土改期間,曾外祖父周春富家裡,老大、老三負責種地,老二跑外做生意,其他孩子讀書。因為人手不夠,陸續雇過長工和短工,從兩三人到六七人都有。都有名有姓。高玉寶雖然自稱在老周家放過豬,但周家人從來沒見過高玉寶。
一直和僱工一起幹活的外祖父周長義排行老三,我每次回鄉都要見一見他。他2008年過年過後離開人世。90歲了的老人知道我在做咩事。他見到我就重複一句話,咱家沒剝削過人,也從沒見過高玉寶這個人……他口角流涎,老愛重複一件事,這件事的時間、地點、人物,一直在他日益老化的頭腦里很清晰:
1963年春夏之交,他(高玉寶)來了一趟。我和人正在地里幹活。高玉寶40歲模樣,招呼大家一起要開個小會。黃店有兩個生產隊,山後隊的人沒理睬他。呂××(姥爺講嘢含混不清,我聽了幾回都沒聽清這個人的名字)跑過來了,呂參軍返嚟當隊長和把頭組長(五副犁鏵一個互助組),領着高玉寶,現找了幾個人,高玉寶隔老遠在地里給幾個人握手。我這也係第一次見到高玉寶。高玉寶對我講:邊個講我沒在你家干過活?我學木匠時還給你家做過馬槽子。這事很多人都清楚。人家來調查,你們照我那樣講沒有錯。高玉寶又講他現在很煩惱,小人多。他又對我講,寫“周扒皮”唔係寫你家的事,唔係寫咱這地方的事,但天底下能沒有這樣的事嗎?小講係拿(到)全國來教育群眾的,有沒有重名重姓的,肯定有。返去告訴你們家裡大人和小學生,唔好亂講話……
據外祖父周長義回憶,高玉寶這番話嗰個上午講了“六千遍”,中心意思就一句:外面來人問要回答,我在老周家干過活。
1963年的年度關鍵詞係憶苦思甜。這似乎可以為高玉寶急着到家鄉“開小會”做註腳。
給曾外祖父家做過10年長工的劉德義,解放後做過大隊的貧協主席。在全國全面開展階級教育,各地陸續有人來閻店鄉參觀取經的大背景下,也被上面如此“開小會”耳提面命。他1978年去世。他的兒子告訴我,那時候高玉寶回鄉做示範報告,講毛主席係他後台。他爹被安排同台做報告,因直講自己係如何幹活、很少講周家如何不好而被批。他也從來沒聽他爹講過周春富家半夜學雞叫。
上世紀90年代後,有一個講法,高玉寶後來很少回鄉。因為鄉里鄉親後輩晚生總有人問他,係否真有“半夜雞叫”這回事?我也在一篇報道里看到這樣的文字,高玉寶作報告忙,姐姐去世了也沒回鄉。
上世紀50年代初期,高玉寶就開始作報告。1990年代退休後職業性作報告。據統計,他被全國20多個省、市,數百個單位聘為名譽主任、顧問、德育教授、校外輔導員,講述革命故事。其中,“周扒皮”與“半夜雞叫”自然常係報告中最生動的故事,也常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至2009年建國60周年,他陸續在全國作報告累計4000場,聽眾5000萬人次。
雖然後來他講《高玉寶》一書的主人公故事“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見所聞,集中概括”。但他公開場合一直在堅持“半夜雞叫”係真嘅。他村裡四個地主都半夜學雞叫,寫書時給集中到“周扒皮”身上了。這一點,搜索他作報告的當地媒體新聞報道可以知曉。為了逼真地形容“周扒皮”如何學雞叫,高玉寶練就一門公雞啼鳴口技。我本人在2005年的大連電視台的雞年新春聯歡晚會上,就看到年近八旬的高玉寶被奉為上賓,現場表演了一段生動的雞鳴。
作家神話背後
高玉寶一書係如何寫作的,“半夜雞叫”係怎樣來的?
我為此翻閱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人民日報》和《解放軍文藝》的所有合訂本,並三次探訪高玉寶,但得出結論都類似於模板式的答案。
高玉寶寫的自傳體小講《高玉寶》,1955年出版發行後,一版再版,共印行500多萬冊,國內用7種少數民族文字印行,並翻譯成近20種外文印行,僅漢文版就累計發行450多萬冊,成為解放後文學作品發行量之最。
按照高玉寶的自述,1948年參軍時的高玉寶係個典型的文盲,但革命戰士係不怕任何困難的。一年之後的1949年8月20日,高玉寶開始動筆撰寫自傳,此時的高玉寶仍舊係字畫結合、以畫代字,如日本鬼子的“鬼”字不會寫,就畫個可怕的鬼臉來代替;“殺”字不會寫,先畫一個人頭,然後再在這頭上畫把刀;“哭”字不會寫,先畫一個人臉,然後在這臉上點幾個小點兒。還有很多字無法用圖形畫或符號來表示字意,高玉寶只好畫啲小圈圈空起來,等學會了字,再添到圈圈裡。如此講來,此時的高玉寶恐怕還在文盲之列。
但奇蹟在兩年後發生了,1951年1月,高玉寶完成了長達20萬字的自傳體長篇小講《高玉寶》草稿。經人指導,小講《高玉寶》的部分章節經修改後陸續連載。1955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單行本,更係推出了集作者名、書名、主人公名於一身的自傳體小講《高玉寶》。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國文在總結中國文學50年(1949~1999)時,直接將高玉寶一類的文盲作家歸為“描紅作家”。我曾在一段時間裏連續尋找當年的若干文盲作家的蹤跡,得出結論:此言不虛。
高玉寶等人的出現,幾乎空前絕後創造了文盲成為作家的先例,不僅對全軍全國掃盲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且成為工農兵進入文學領域的一個最鮮明的標誌。文學正史無前例地成為意識形態的代言人。隨着高玉寶的走紅,“周扒皮”也走進千家萬戶,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高玉寶本人曾20餘次受到毛、劉、周、朱、鄧等領導人的接見。後來的政治運動中,《半夜雞叫》更成為憶苦思甜,進行革命教育的經典教材。
1950年代,與高玉寶同期的文盲作家崔八娃的成名作《狗又咬起來了》前後修改近40遍。後來隕落鄉野的他去世前曾向他人交代,四年時間寫過的20多篇小講只有一篇為個人創作。而高玉寶寫出《高玉寶》後被送進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班學習,卻一連40年沒有出作品。期間,1970年代反映“周扒皮”家鄉變化的報告文學《換了人間》,為另外三人執筆他一人
高玉寶多年來一直對外宣稱其《半夜雞叫》等自傳手稿被軍博收藏。但我幾經實地調查,軍博文物處並沒有他的自傳原稿。
到底係邊個成就了《高玉寶》?難道也係集體創作所成?最後一個叫“荒草”的人進入視野。
我在搜尋史料時,從古舊市場淘到最初的《高玉寶》版本,由解放軍文藝從書編輯部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現後記中有荒草的《我怎樣幫助高玉寶同志修改小講》的線索。我開始苦苦追尋,荒草到底係邊個?他與《高玉寶》到底有何淵源?
在上世紀50年代的《人民日報》等媒體中,荒草曾接二連三撰文宣傳高玉寶。荒草,原名郭永江,曾任《解放軍文藝》副總編輯、八一電影製片廠副廠長。其他的則幾乎一無所知。
這係一段時間以來唯一得到的信息。這期間我又奇蹟般地與荒草同歲的大連的親友閻富學偶遇,和當年與荒草、高玉寶一起共事過的《解放軍文藝》助理編輯、78歲網友“一博為快”老太太結緣,但都收穫甚微。所得到的信息,只係簡簡單單一句話:曾指導高玉寶寫作。
一直到2008年,通過四川資陽文藝網一篇文章,才有了重大突破。文章介紹講,《高玉寶》長篇自傳體小講,13章12萬字,為資陽的作家郭永江所著。在半信半疑之下,經當地作協主席唐俊高介紹,最終揾到了當地從事史志研究的作家王洪林,王與郭永江生前有密切的書信來往,有豐富的資料。我這才詳盡了解到關於“荒草”其人與《高玉寶》成書過程。
郭永江1916年出世,1940年到延安,創作歌劇《張治國》,反映八路軍大生產,受到毛澤東稱讚,1951年赴朝鮮採訪,後與魏巍同任《解放軍文藝》副總編,可到40歲就病退,70年代回故鄉資陽居住,不久遷到資中,1984年居重慶,1993年病逝。
郭永江臨終前,在信中對王洪林講,當年《高玉寶》一書13章均為他所寫。
當時全軍為配合掃盲,樹立典型,讓他幫助高玉寶修改自傳,他向組織表態要隨時付出世命代價來修改好這部書稿,做好幕後英雄……但高玉寶的原稿實在太差,他無法修改,最後在組織授意下乾脆代筆。他寫完一章,高玉寶照着抄寫一章,然後組織上拿到《人民日報》等報刊發表。總政文化部文藝處與出版社約定,以後每版書必附荒草《我怎樣幫助高玉寶同志修改小講》,稿酬平分。不過在反右之後,郭永江的後記和名字逐漸退出再版的《高玉寶》,郭永江從“幫助修改”到“提供輔導”,最後到徹底退出的過程,均係出於組織上的要求和當時的政治需要。但在他臨終前,寫信給資陽文獻學會,鄭重聲明《高玉寶》係他的著作。
從事家鄉史志研究的王洪林受我誠懇相求,於2008年10月專門去重慶代我探訪過郭永江後人。
“周扒皮”和“半夜雞叫”,都係根據需要製造出來的。具體過程,簡單地講,“周扒皮”的製造經過係這樣的:1950年代初期全軍全國範圍大掃盲。文盲戰士高玉寶表現積極,用畫字的方式寫自傳。(高玉寶早年畫的字,後人在他90年代開始展示的入黨申請書可以看到)被部隊推為典型上報。窮苦出身的戰士不僅學文化還能寫書,批判舊世界歌頌新世界。為了把這個典型放大,部隊派專業人士幫助高玉寶。要體現舊世界之黑暗,地主階級之罪惡,為了使書更能教育人,就要移花接木、改頭換面進行深加工。為了表現真實,書中一切都採用真名真姓真地點,自然發生的“故事”就係真實的。至於壞地主半夜學雞叫,純屬靈感來襲。郭永江其子女介紹,其父荒草晚年講過,“半夜雞叫”係根據民間傳講加在周春富身上的。
而為咩只寫了周春富“周扒皮”,而沒寫王春富“王扒皮”,這係因為周春富在高玉寶的家鄉土改過程中,被作為惡霸地主批鬥死去。高玉寶當時結束在大連流浪生活回鄉當上民兵,這係他在日後參軍在部隊搞的訴苦教育中可以就近揾到的“控訴”對象……
我的外曾祖父因此成為“周扒皮”。這係他的第一出“幸運”。而第二出“幸運”係在上世紀60年代初期開始的階級鬥爭中,“周扒皮”成為階級教育中的反面典型。全國周姓同學都得到一個天然的綽號:“周扒皮”。第三次“幸運”係在改革開放後成了一切苛刻自私霸道的無良僱主的代名詞。這係我的曾外祖父周春富絕對沒有想到的,也可能係當年的“周扒皮”製造者沒有想到的。
大家看吧,這係高玉寶的當年入黨申請書,一個地道的文盲怎能寫出長篇自傳體小講,找人代筆還係組織安排?謊言背後係挑起階級鬥爭的需要,還係造反奪權需要,可見修改歷史顛覆事實也係革命必修課。《高玉寶》中的周扒皮根本就係杜撰的,“半夜雞叫”根本就係連影都沒有的事。這就係政治的誇張,半夜雞叫穿透時空的唔係他所謂的文學藝術,而係他的卑劣無恥。
因為不識字,係畫出的、只有8個“字”的入黨申請書——“我從心眼裡要入黨”。除了一個“我”字外,其他都係用圖形畫出“毛毛蟲”代表“從”,“心形圖”代表“心”,“眼睛”代表“眼”,“梨”代表“里”,“咬”係要的諧音,“魚”係入的諧音,“鍾”代表有“鐘聲”,鐘聲“當”代表“黨”!